

当前我国经济在增长速度趋降的情况下,新旧动能交替的现象十分突出,不仅每增长1%包含了更大的绝对量,而且7%不到的增长率内含了比过去质量更高的经济总量。其内在的动因是发展进入新常态后,促进经济分化的趋势不断增强、程度不断加深,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资源配置扭曲的状态不断得到修正,产业转型升级的效应也不断地显现。
从区域增长格局看,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强势企稳回升,但东北和中西部一些地区依然困难重重,处于冰火两重天中。从产业部门看,总体上低端技术、低附加值的、高消耗的实体制造部门衰退明显、步履艰难,但高技术产业部门、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一枝独秀,亮点频繁闪耀。2016年,仅采矿业、高耗能行业的生产增速回落幅度较大,而高技术产业则以近似两位数的速度增长,其中医药制造业、计算机、通信等制造业增长尤快。这种经济分化,说明了什么呢?
第一,进入新常态的表象是速度降低,本质特征却是有增有减、有上有下:有效益、有质量、有环保的速度上去,而无效益、低质量、污环境的速度降下去。这是贯穿发展新常态下经济新旧分化的基本逻辑。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例。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名义增长8.1%,尽管投资增速趋缓,但结构持续优化:第三产业投资增长10.9%,比第二产业高7.4个百分点,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5.8%,增速快于全部投资7.7个百分点。科教文卫领域投资比上年增长19%,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8.3%。同时新动能的发展力量不断积蓄,工业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1.7%,工业技改投资增长11.4%。
第二,新常态下结构变化的表象是比重和数量上的变化,本质特征却是结构优化下的提质增效:一是服务业增速继续快于工业,形成了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。2016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1.6%,比上年提高1.4个百分点,高于第二产业11.8个百分点,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0%左右。二是工业内部高附加值、低消耗、低排放产业的比重持续上升,技术含量不断提升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0.5%,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高4.5个百分点。三是工业企业效益明显好转。主要表现在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增长4.9%,扭转了2015年利润下降2.3%的局面,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达5.97%。这些都体现了6%多一点的增长速度,要比8%以上的速度质量高、结构优,是转型升级要实现的主要目标。
第三,新常态下发展动力变化的表象是投入要素的转换,本质特征却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。依靠增加要素投入获得的增长并不能持续,更持久、高速的增长,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增进。目前我国经济增速放慢的背后,其实是全要素生产率不断降低的结果。而某些替代性的新动能的不断涌现,则是这些领域全要素生产率迅速上升所致。未来,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,即在既定要素投入下推动产出持续地增进,需要扭转要素配置扭曲,实现资源从低效率企业、部门、地区,向更高效率的企业、部门和地区移动;同时根本上还是要靠密集的研发投入和高强度的技术创新。
比如,2016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广东和上海,经济发展新动能就是源于新产业的崛起:2016年广东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76.3%、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45.2%;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、商务服务业,以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5.3%、18.3%、19.9%。上海则主要得益于自贸区改革红利不断释放,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,特别是金融等服务业快速发展,如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9.5%,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70.5%。其中金融业增加值4762.50亿元,增长12.8%。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1618.58亿元,增长15.1%。
经济分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,增长速度高位下行后的必然结果。因为:
第一,在高增长的繁荣时期,受快速扩张的需求拉动,资源往往会根据盈利信号向高收益的产业集中,这种投资的趋同,必然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同构化。在进入需求收缩的增长周期里,过大的产能便会争夺不断缩小的市场容量,表现为严重的产能过剩和过度竞争的格局,残酷的市场竞争必然带来产业内、地区间企业的业绩分化。这是无法避免的。
第二,在高增长的繁荣时期,受急速扩张的需求拉动,产业内的每个企业都可以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,都可以生存下去而不被强制逐出市场。“只有潮水退却时,我们才会发现究竟谁在裸泳”。但在需求低迷、产能严重过剩的产业中,只有效率高的企业才能续存下来,出现“市场份额向品牌企业集中,效益向规模企业集中”的分化现象。
第三,在高增长的繁荣时期,巨大的市场需求使产业内的企业不需要通过创新,甚至不需要提升成本效率也能安然无恙地生存。而在需求低迷时期,有的企业会为资源寻找新的去处,从事新产品、新商业模式的创新;有的成了僵尸企业,缩头冬眠;有的则停留在原处等着熬着,指望着什么时候经济景气度上升。这些情况形成的分化趋势,显然是市场规律使然。
推动经济加速分化,是推进发展新动能崛起的出发点和前提。在择优分配的规则下,如果严重的过剩产能不能消除,僵尸企业不死,效率差的企业不能顺利退出市场,市场就不能出清,就要继续占用或者消耗物资资源、信贷和市场,而优秀的企业就不能获取更多的发展资源,发展的新动能就不可能崛起,最终阻碍的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。因此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,就是要让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,通过市场竞争,加速经济分化,形成新的经济结构,实现新的高水平的市场出清。这意味着分化越快越好,为经济增长寻找到新的边际动力,才能节省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时间,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的社会成本。
既然经济分化不可避免,既然分化有利于中国经济进入最佳的调整和增长的轨道,那么对于各地区、各行业、各企业来说,与其抱怨现状,不如思考行动;与其苦熬,不如苦干。从抱怨经济分化和消极等待,全面转向埋头苦干、主动推进经济分化,重要的是要认清形势,提高思想认识和明确政策取向:
第一,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度,全面理解、认识和处理现阶段的经济分化问题。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,是现阶段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使命。促进经济分化,就是实现这一使命的具体的发展手段。在战术上,要通过推进经济的迅速分化,最大限度地降低发展的社会成本,以短痛换取忍受长期的折磨。
第二,要主动适应新常态、重视创新和提升质量效益。实践证明,凡是主动适应、引领发展新常态的,重视创新和质量效益的地方和企业,其发展态势都比较好;反之,压力和困难就会比较大。这一发展新常态目前正在深化。未来我国将不断冒出更有活力的地区、更具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,但同时有些地区、行业和企业日子也会越来越难熬,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和行动准备。
第三,推进经济分化的根本原则,在于破除预算软约束。软预算约束机制是市场出清的主要障碍,是阻止经济分化的主要的制度性力量。预算约束不硬,就无法让资源按照市场竞争规律流动,无法淘汰落后产能和低效企业。如果市场主体在投资决策时,从不用担心失败后的退出,以及不用担忧被追究决策责任,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驱动资源自动进入创新领域,反而会使经济风险日积月累。
第四,要以精准的产业政策引导经济分化和资源流动。产业政策在现阶段的功能,应该主要定位于弥补市场失灵和失败。它的作用是要解决因市场缺陷而忽视公共利益的问题。同时也要把握好产业政策作用的方向和主要内容,重点是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,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。在中高端共性技术、人力资本供给等方面,提升生产要素的质量,鼓励技术创新的政策氛围形成。
本文原载《中国社会科学网》
作者简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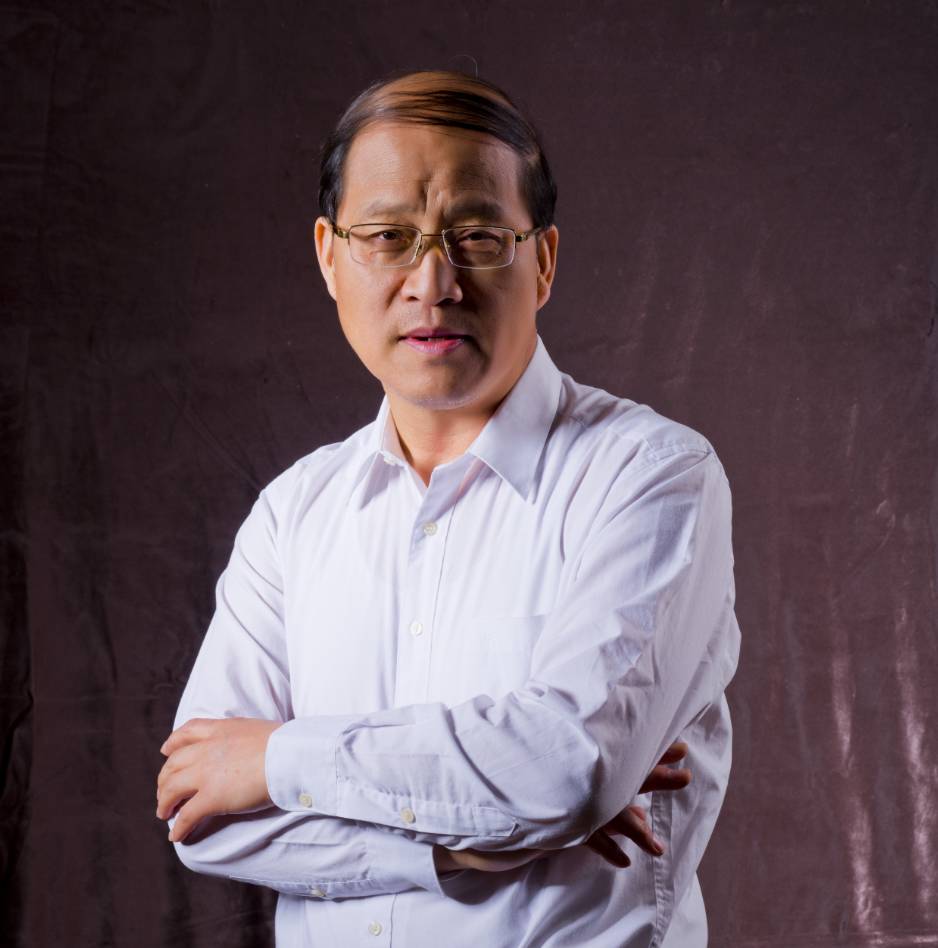
刘志彪,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、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、南京大学教授、长江学者特聘教授。
来源:产经快评
